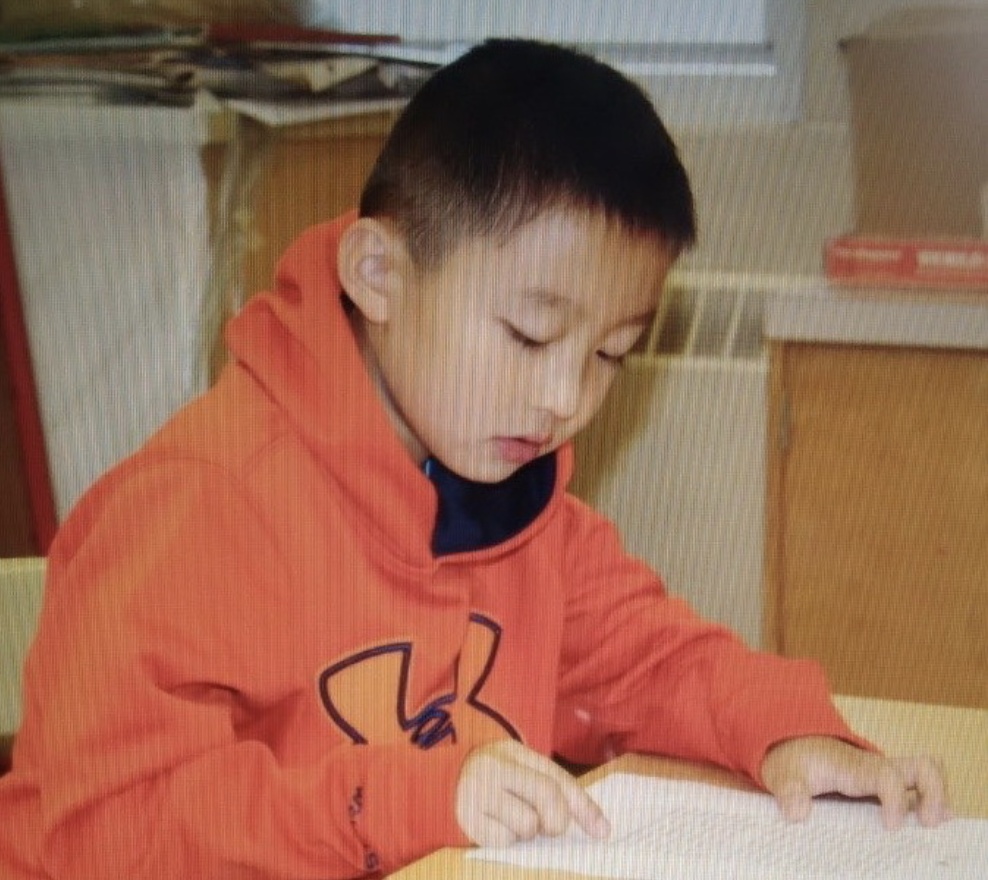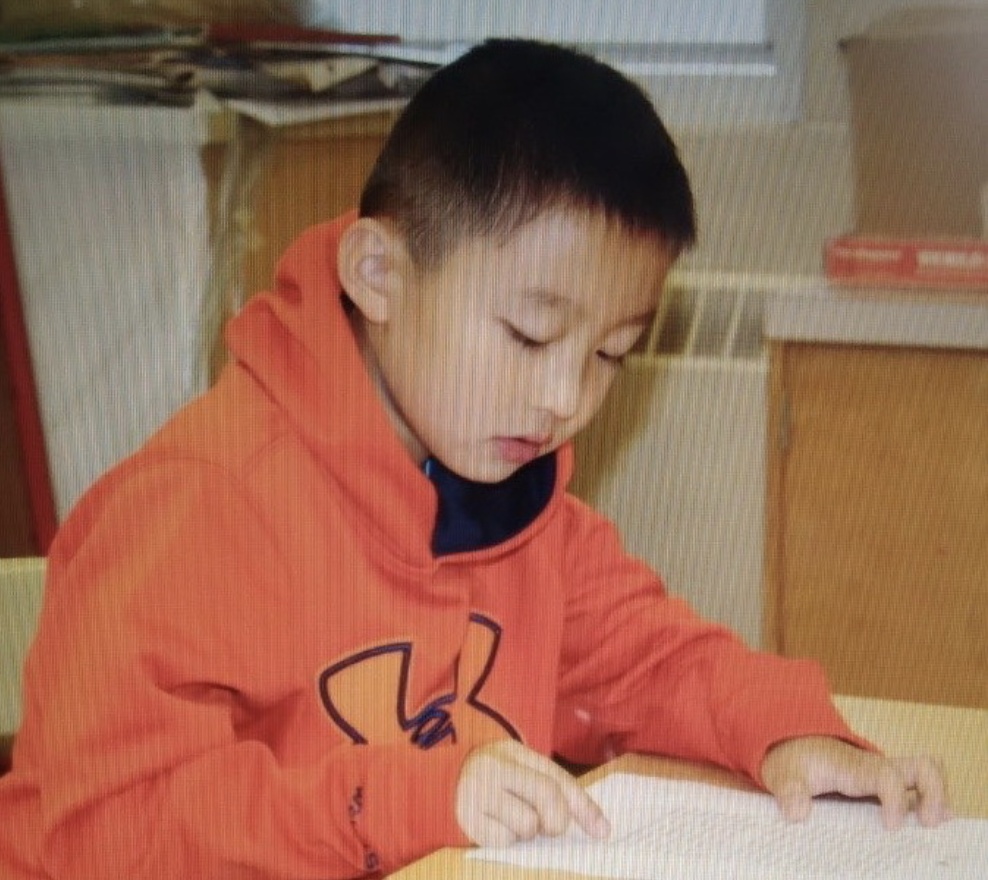【人民報消息】少典一出生就非同凡響。
據大紀元記者伊鈴多倫多報導,2008年10月最後的一天,在多倫多一家醫院的產房內,醫生、護士進進出出,神情緊張,他們正焦急地等待一個嬰兒的出生。
躺在產床上的萬力是某國際媒體加拿大分社社長,這是她的第二個孩子,預產期已經超過1週,這天早上,醫生給她打了催生藥,直到下午5點,孩子還沒生下來。
突然,胎兒的心跳從每分鐘150次降到50次以下,明顯胎兒缺氧,情況萬分危急,必須儘快讓孩子生下來。
醫生、護士一陣緊張的忙碌之後,孩子終於生下了,是個男孩,渾身青紫,小手緊緊抓住自己的臍帶,已沒有呼吸、心跳……
時間刻不容緩,醫生、護士實施緊急搶救。終於,一聲微弱的哭聲響起,打破了產房裡緊張的氣氛,大家如釋重負,個個喜笑顏開。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之戰,打贏了!
經歷了一整天的分娩,萬力已疲憊不堪。看著眼前的兒子,粉白、嬌嫩,大眼睛溜溜轉,可愛極了,萬力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少典的出生,給家庭帶來了更多的歡聲笑語,爸爸、媽媽、姐姐都很寵愛他。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少典越長越大,越長越漂亮,長睫毛、大眼睛,笑起來陽光燦爛,是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寶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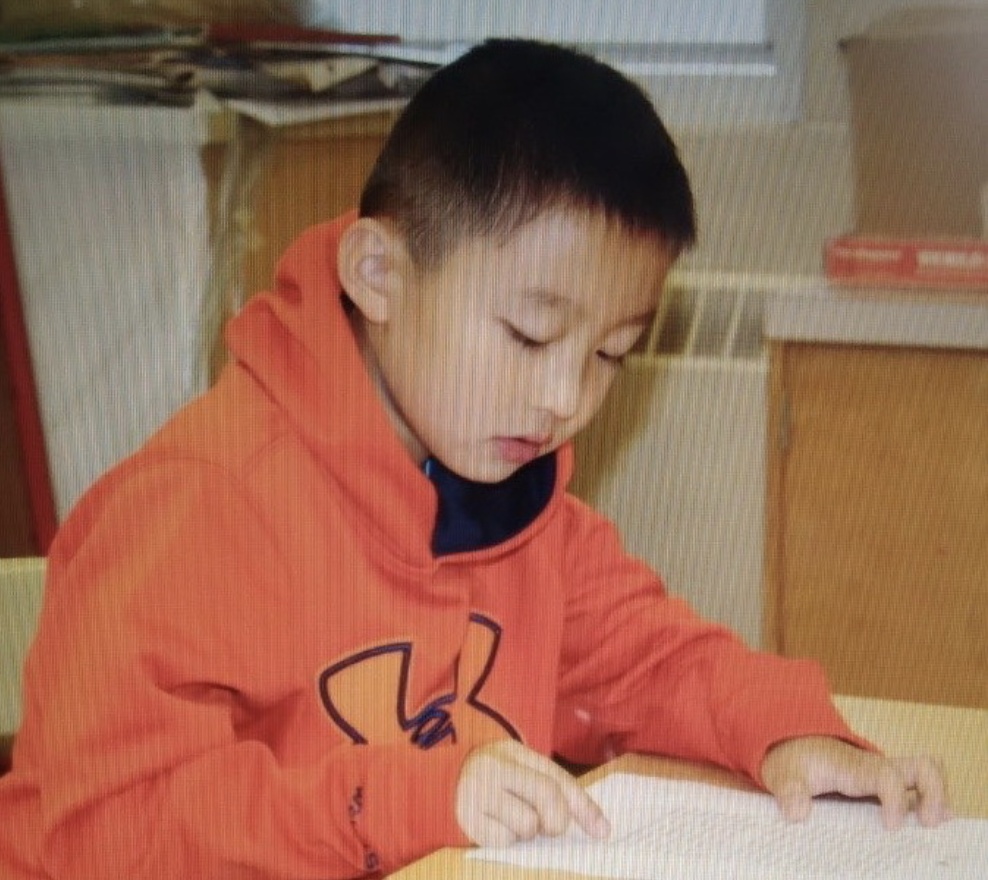 一封信的衝擊
一封信的衝擊
很快,少典4歲了。萬力發現,同齡孩子能嘰嘰喳喳地跟父母交流了,而少典說話還不太順暢。他吐字緩慢,每發音幾個字就會被卡住,後面的意思無法表達。萬力沒多想,以為少典年紀還小,沒關係。
轉眼少典上小學了,無論在學校還是家裡,少典都是個乖孩子,特別聽話。但他的語言能力和學習能力已表現出明顯的障礙,他無法順暢表達自己的想法,無法專注學習,成績也跟不上進度。
一天,學校老師和校長約見萬力,告訴她,孩子可能有輕度自閉症,建議把他送到特殊教育學校。
現代醫學認為,自閉症是因先天腦部異常,進而引起的一連串發展障礙。自閉症兒童主要表現為在社交、溝通和行為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缺陷和挑戰。
萬力沒有聽從校方的建議,她認為自己的孩子沒問題。在她看來,小孩就像一粒種子,每粒種子的開花期不一樣。少典可能屬於那種遲開花的種子,是小笨鳥,只要他的品質好,總有他的花期,總有一天要開花的。她決定順其自然。
少典上小學三年級了。一天,萬力接到來自學校的一封信,大意說,學校要參加加拿大安省教育局的EQAO考試。教育局會根據學校的考試成績排名次。明天學校有這樣一場考試,讓少典不要來,因為少典的考試成績會對學校的排名造成很大負面影響。
這封來信如同晴天霹靂,萬力非常震驚。學校怎麼能這樣做?這不是明顯的歧視嗎?她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孩子。
在安省,公立小學的學生每到3、6年級時,都需要參加安省統考。這個測試由安省教育獨立機構——教育質量及問責辦公室(Education Qu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Office)負責,稱為EQAO考試。
EQAO評估是安省教育計劃的一部分,用以協助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與成效,判定是否需要額外幫助。如果學生未能達標,老師和家長則會討論如何幫助該學生縮小學習差距,提高成績。另一方面,EQAO評估也加強了安省公立教育系統的問責制度。
那天早上,少典像往常一樣,背著小書包站在門口,等待爸爸媽媽送他上學。
此時,爸爸走到他跟前,說:「少典,今天你不用去學校。」
少典抬起頭,睜著大眼睛看著爸爸:「為什麼?爸爸?」
爸爸看著他,鄭重其事地說:「今天學校有一場考試,只有最出色、最善良、最乖的孩子不用參加。而你就是那個最出色、最乖、最善良的孩子。因此,你今天不用去,可以在家裡玩一天。」
少典聽了爸爸的話,非常驚喜,說:「真的嗎?爸爸,真的嗎?」
爸爸認真地點點頭,說:「是的,是真的。」
天真的少典馬上轉身,歡欣鼓舞的樣子,蹦蹦跳跳地回到屋裡,放下書包,自己玩去了。
站在旁邊的萬力聽著父子倆對話,又看著孩子那張天真無邪的臉,她再也無法自持,淚流滿面……
一整天,萬力都在流淚,腦海裡全是少典那雙清澈明亮、天真、無辜的眼神,還有父子倆的那段對話。
這件事給萬力當頭一棒,她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那天起,她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孩子未來怎麼辦?他的前途如何?
無法逃避的壓力
為了孩子,萬力賣掉了在多倫多富豪山莊的房子,搬到多倫多東北邊較遠的小鎮Oxbridge。(萬力提供)
這件事情過後不久,萬力迅速決定:搬家。
2017年,萬力賣掉了在多倫多富豪山莊的房子,搬到了多倫多東北邊較遠的小鎮Oxbridge。在她看來,小鎮的學校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壓力,兒子在那裡能快樂地成長。
少典善良、單純、內向又靦腆,與世無爭;加上學習障礙,溝通困難,成績不好,他常常受到同學的孤立、歧視、甚至霸凌。
萬力經常接到老師的電話,給少典送換洗衣服,原因是他被同學推到校園的水窪裡。有時候少典回家,身上都是尿臊味,因為一些小朋友老往他身上撒尿。
少典對同學的霸凌從不回應,人家欺負他,他就躲開。媽媽告訴他,下次同學欺負你,你就告訴老師。可少典一旦遇到事情找老師,他表達不清楚,老師也沒耐心聽下去。
萬力是一位法輪功修煉者。1996年,萬力大學畢業,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法輪功,從此走上修煉之路。她親歷過1999年的「4‧25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同年又經歷了「7‧20」中共全面打壓法輪功,但她從未動搖信念,一直是「真、善、忍」的堅定信仰者和維護者。
在家裡,萬力也會帶兒子一起閱讀法輪功著作《轉法輪》,儘管這對少典來說相當困難,但母子倆還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讀。平時少典受了欺負,爸爸告訴他,誰要打你,你就打回去,打出問題,爸爸擔著;可是萬力經常教育兒子,修煉人不能和常人一樣,別人欺負你,會給你德,拿走黑色物質業力。但少典聽不懂,只能跟他講,白色物質是好的,黑色物質是壞的。
每次見到老師,萬力總會聽到:你兒子是個特別好的孩子,特別可愛,愛幫助別人,經常主動幫助同學,幫助老師,但就是成績不好。
怎麼辦?每次聽到這些,萬力都無言以對。這是孩子的自然狀態,她無能為力,沒有辦法硬逼孩子改變什麼。只是孩子的將來怎麼辦?他的未來是什麼?
日益增加的憂慮如同揮之不去的魔咒,時刻籠罩在萬力的心頭,她被困擾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中。
報考飛天藝術學院
少典八年級畢業了,其他小孩獲得最佳數學獎、最佳物理獎、最佳優秀畢業生獎,少典獲得最佳愛幫助別人獎。萬力全家人都去為少典祝賀、鼓掌。
少典雖然有語言、學習能力障礙,但他有運動天分,從小就被送去學跆拳道、游泳、打籃球。他在運動中表現很出色。籃球教練和游泳教練都希望他走專業路線。當時少典已經在一些專業俱樂部接受訓練了。
少典從小看神韻,每年都看好幾場。他很喜歡舞台上那些大哥哥們跳舞,還跟媽媽說:「等我長大了,也要去神韻。」
眼看少典要上高中了。一天,萬力問他:「你想去神韻嗎?」少典點點頭,說:「想,非常想。」他們很快向飛天藝術學院遞交了申請材料。
2022年8月,萬力陪兒子去學校面試。
主考官問他:為什麼想來神韻?
少典回答:「助師正法」。
主考官說:記住你今天說的話。
那一天特別順利,少典被錄取了。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少典一邊寫,一邊哭,直到回來的路上,他還在哭。萬力問他:「為什麼哭了?」他告訴媽媽:太激動了。
少典很快進入飛天藝術學院讀書。入校的那個晚上下著大雨,飛天的老師帶幾個同學來接少典。這位平時很粘媽媽的少年,連說聲再見都忘了,自己拖著行李箱,歡歡喜喜跟在老師後面進去了。
驚喜
少典去飛天藝術學院後,萬力會定期去看他,每次接他出來,首先出去吃飯、購物,然後把他送回學校。每次去,她都看到孩子的變化,臉上的笑容越來越陽光。少典也告訴媽媽:這裡每個人都很好,很友善,他很喜歡這裡。
大約三個月的時候,萬力去看望他。這一次,少典一出現,萬力立刻感覺眼前一亮,變化好大啊,他瘦了20磅,膚色白裡透粉,身姿挺拔、高挑、帥氣,渾身散發出從未有過的自信,完全像一個專業舞蹈演員的樣子。
回到酒店,少典說:「媽媽,我們能不能先學《轉法輪》,然後再出去?」隨後他拿出正體字版的《轉法輪》,流利地讀起來。
萬力看著兒子,驚訝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向中文水平很差,過去讀《轉法輪》都是她帶著,你一句,我一句,讀得磕磕巴巴。來了飛天三個月,他居然主動要學法了,還能通讀正體版本,而且讀得非常流利,只偶爾碰到不認識的字而已。
看著媽媽驚訝的表情,少典笑笑說:「媽媽,你是不是覺得我中文進步了?」
「是的,是的,兒子,真沒有想到會這樣,你真的太棒了。」萬力趕緊說。看著這個13歲的孩子,她欣喜不已,「這太不可思議了,真是神奇,是神跡。」
 提高心性
提高心性
從那以後,少典不僅專業技能提高很快,語言能力也飛速進步,他能跟媽媽聊一些內心的想法和感受,聊他修煉上的問題,比如:如何過心性關,如何提高心性等。
少典以前在外面老受欺負,在家爸爸、媽媽、姐姐就特別寵愛他、保護他,這讓他多少有些嬌氣。舞蹈訓練很艱苦,特別是毯子功訓練要翻跟頭。開始時,他會有些害怕,他就去怕心,讓自己變得更勇敢。
母子倆經常在修煉上交流,萬力告訴兒子:「有執著心很正常,正因為我們不完美,所以才需要修煉。修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個過程。慢慢去掉執著心,它就會越來越少。」
少典後來當了小班長,又當了大班長,這個過程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面對一些同學不服從安排時,他也會生氣、發脾氣。但他很快意識到,生氣和發脾氣都是向外找,應該向內找。他意識到自己應該更加關心同學,體諒他們的難處和需求,站在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在跟同學互動中,少典主動克制,去除攀比心、妒忌心、爭鬥心。
少典在修煉上越來越成熟,碰到任何事,無論是身體上的、心理上的,他都會第一時間站在修煉人的角度,向內找,能夠時時刻刻地把自己的一絲一念放在修煉上。這一切在去飛天藝術學院之前是不存在的,這是他最大的改變。萬力為此特別欣慰。
孩子變了,萬力也變了。過去那些時刻縈繞在她心頭的憂慮徹底消失了,她從那些擔心、焦慮和壓力中徹底解脫出來。
半年前的一天,少典給媽媽打電話,說:「媽媽,我終於能聽懂師父說的話了。」還說:「我要是能早一點聽懂師父的話就好了!」
這一天,少典好像突然在人間開竅,彷彿過去就像一場夢,他徹底醒了,一切恢復正常。
如今,少典已經就讀飛天藝術學院2年級,是一名神韻見習演員,目前正在隨團巡迴演出。
「孩子的變化,簡直就是一個神跡。」萬力說,「對於神韻,對於飛天藝術學院,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誰會拿自己的孩子做試驗呢?」
近期,《紐約時報》連篇發文,攻擊法輪功創始人和神韻,這讓萬力十分震驚。她向讀者分享自己和孩子親身經歷的故事,也想通過大紀元向《紐約時報》發問:「誰會拿自己的孩子做試驗呢?」
第一,環境問題
萬力說,無論什麼信仰,無論什麼文化背景,天下父母的心是相通,那就是對孩子的愛。沒有任何一個母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快樂、健康,也沒有任何一個母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個特別友善、能獲得進步的環境中生活。因為這不是別的事,不是生意,也不是工作,而是你的孩子。
無論想把孩子送到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家長都會事先對學校進行了解、調查。如果對一所學校完全不知情、不信任、沒有正面的認識,家長怎麼可能把孩子送過來?沒有任何一個母親會把自己的孩子當作試驗品。這是個常識問題,這個邏輯不言而喻。
萬力說,在去飛天藝術學院之前,少典作為一個問題孩子,他在學習、溝通、社交方面有許多障礙和困難,他在學校裡有很大壓力,身心不健康,他不開心、不放鬆。但是他去了飛天藝術學院之後,在那種修煉氛圍中,除了專業技能的學習,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友善、健康、放鬆,非常正面,他本人非常享受那種生活。
她說,經過了這兩年學習,少典完全變了一個樣。他開朗了許多,學習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加上他對舞蹈的熱愛,他在這裡有了充分施展的空間。「作為母親,孩子有這樣的改變和提升,我真是打心眼裡很放心,我的心一下就放鬆了。」
萬力說,《紐約時報》歪曲神韻的社會價值。在一個藝術演出大環境非常不好的時代,神韻能夠異軍突起,從一個團發展到八個團,並且非常受歡迎,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神韻作為一個世界一流的演出團體,她所帶來的美學上的享受和傳統道德價值的傳承,讓整個社會受益。」她說,「我兒子在神韻就非常受益。」
萬力真心希望《紐約時報》的編輯、記者們,秉承負責的態度,坐到神韻的劇院裡看一場現場演出,問一問身邊看過神韻的朋友,接觸一些神韻孩子的家長,聽一聽他們的感受。然後就會知道,他們發表的文章有多麼不顧事實,是錯誤的認知和偏見。
第二,廉價報酬問題
《紐約時報》攻擊神韻使用學生演員,報酬低微,萬力為此特別做過調查研究。
像少典這樣上初中、高中年齡的孩子,如果去一個專業藝術學校學習,首先家長付學費、生活費、住宿費和一切跟舞蹈專業有關的服裝、耗材,正常情況下,這些費用一年要付大約10萬美金。
如果孩子要去另外的城市或國家實習,家長還要負責孩子的機票、酒店、吃飯和各種演出服裝費用,這些費用也是一大筆錢。
而且,在實習過程中,不會有任何人付你工資。因為實習是經驗的增長,人家給你實習的機會,就是對你最大的幫助,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者機構會付給你工資,你可能還需要為獲得這個實習機會付出很多錢。
但是在飛天和神韻這裡,家長沒有付學費、住宿費、演出服裝費,跟實習有關的酒店、飛機票、演出服裝等,家長沒有掏一分錢,而且孩子每個月還有補助。
也就是說,家長不用給孩子付出任何東西,而孩子不僅獲得了實習經驗,還在世界各地增長了見識。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他需要自己去解決。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講,孩子都有一個長足的進步和成長。
走到哪裡都很難尋找到這樣的實習機會。神韻完全可以一分錢都不給,所有的錢都要求父母出。因為無論哪個藝術學院都是這樣做的。
萬力說,《紐約時報》作為一個百年大報,立足於北美,對美國的教育體系應該非常熟悉,甩出這樣一個結論,真的令人非常震驚。
第三,保安問題
萬力說,在美國,任何一所住宿私立學校,對於那些未成年的學生來說,學校就是他們的監護人。只要是那種負責任的、在家長和孩子們心中注重教育質量的學校,它都會在安全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必須對孩子負責任,任何私立學校都不可能隨便讓陌生人進去。
飛天藝術學校建在一座山上,跟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為了孩子的安全,一定有界線劃分,這樣做家長才會放心。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中共對法輪功慘無人道的迫害已經持續25年,從來沒有停止過,一直在破壞、威脅。現在又把這種迫害延伸到海外。比如中共特務到神韻演出劇院恐嚇、炸彈威脅,神韻演出的大巴士輪胎遭劃破,在飛天和神韻駐地的龍泉寺附近進行各種各樣的滲透和破壞,中共特務的這些行徑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對於飛天藝術學院來說,這種保安措施是必須、必要的;對於家長來說,也是必須、必要的。」萬力說。
她說,25年前,中共實施對法輪功在「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殘酷手段,製造「天安門自焚偽案」,捏造1400例死亡案例,栽贓陷害法輪功。現在它們是舊技重演,只不過方法更具迷惑性,手段更毒辣。企圖利用美國的法律和媒體,實施輿論戰、法律戰。但這只是它們最後的垂死掙扎,根本不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