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冬天,伴随著我成长的前十多年一直象冬天一样寒冷。因为父亲被戴上“右派嫌疑”的帽子,我们一家全部受牵连而遭了殃。举个例子,邓小平上台开始改革开放后,我也进入中学。一天母亲拿出一份我在幼儿园时的学期总结政治评语,除了一套革命语录之外,幼儿园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得过且过,笑的太多”。我很不解,就问我母亲,“幼儿园才5~6岁的小孩,哭才惹人烦,我笑得多也是过错吗?”母亲说,“你忘啦?你是右派嫌疑的儿子,你在被罚站时还能笑,被强迫把新椅子换给革命干部的孩子时,你还能笑出来,那些革命老师认为你是跟她们作对。”原来如此,我才五岁就在幼儿园被“专政”了,理由是我父亲仅仅被怀疑是“右派”。
母亲又说,“你能在幼儿园用笑来表示反抗,而在小学时,你经常被罚写检查,还要把检查贴在全校的报栏里,原因也是因为你父亲,还有我们的出生不好,但是你也过来了。现在你进中学了,应该懂事了。”母亲看看我的反应,转入正题,“你们英语老师今天来家访,说你人很聪明,但是太不用功,英语单词背得太少。”
我仍然不以为然的样子,小时候被弄堂里小朋友欺负,在小学被老师欺负的往事早就忘记了,现在“四人帮”也粉碎了,我当然玩的很高兴,哪里还想读英语。但是这份陈年老旧的幼儿园的政治评语却又勾起了心中的隐痛,于是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是右派嫌疑?”母亲说我太小还不懂,以后会告诉我们兄弟,但是要我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永远别回来了。也许十几岁的我已经开始有记性了,以后每次上到英语课,我就会想起那张政治评语,想起以笑代哭的日子,从而强迫自己学好英语,学好英语。
但是我上完大学却仍然无法出国,因为我们家太穷了,交不出三万元人民币的“培养费”。父母亲辛苦工作30多年,拿的是5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所有的“剩余价值”早给党拿去了,这教育培养费不早就交给国家了吗?哪里还拿得出象天文数字一样的三万元呢!
于是我只能先开始工作,第一年实习工资每月62.5元,第二年转正后拿86元一个月,另外还有50元奖金。就这样干了五年,我把所有工资都交给父母,一共存了三千多元。共产党就像榨取我父母一样,开始榨取我的“剩余价值”。后来遇到了一位娴惠的女孩,她不嫌弃我们家的贫穷,我们结婚了。虽然服务国家了五年可以不用交“培养费”了,但是家庭圈住了出国的心。
一晃又过去了五年,在工作和业务来往中,我实在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厌恶共产党领导干部那种台上讲话一付官腔、宴席歌厅一付流氓腔的两付面孔的人格,也为了呀呀学语的女儿有一个纯洁的成长环境,我终于下定决心出国。苦苦复习了一年多英语后,终于来到了美国。而在美国奋斗的压力下,我只想忘记痛苦的过去,直到接到父亲将去世的消息,我才突然又想起了那些被歧视、批判的往事。
兄长在办丧事买墓地时不时打越洋电话来商量,电话里也没有提到任何“秘密”,我以为老父亲可能有什么值钱的古董给了兄长,而我对钱财看的很轻,所以也没有主动问那个秘密是什么。一直等到兄长处理完了丧事回到美国,他才很严肃地在电话里对我说,“爸爸告诉了我一个家族的秘密。”
事情从我的爷爷说起。我从没有见过爷爷,连照片也没有一张。我一直听大人说他抽鸦片把原本富有的家给败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念头想见见爷爷。兄长说,父亲临终讲的家族秘密里,爷爷不抽鸦片,他是一个读过私塾会写些文字的书生。家里有很多地,因为书生不会种地,所以大多数都给了同村的亲戚去种,也不收租。自己家也没有帮佣,父亲种些自己吃的,姑妈做些家务,生活比较清贫,但是也过得去。老实八交的农民嘛,传统里就是要“知恩图报”的。那些拿了地去种的亲戚,平时不交租,过年时多少也会送些糕点或白米来,爷爷也就很高兴了。
爷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我大伯参加共产党“革命战争”,已经是干部了;叔叔也参军是解放军战士了;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和我姑妈一个女儿在家。我的姑妈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平时不下地,自然长的清秀水灵些。但是没想到灾难很快就降临了。村里来了“土改”部队,一个共产党干部领导,还有一队士兵。
土改干部在河北老家是有原配妻子的,但是见到我姑妈后,就起了喜新厌旧之心。父亲说,一天那个干部带著一个兵就到我们家来了,一开口就要娶我姑妈。这些外来的土改干部到村里没几天就杀了不少人。因为江南水乡土地肥沃,只要肯吃苦的农民,多少都能自己买些地,成了自耕农,还自己盖起房子。土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听你解释这地是自己吃苦省出来的,土地多些的就枪毙,冤杀了很多有地的“中农”。我爷爷读过书,也在外游历过,当然就看不惯那种土匪作风了。一听说那干部要休了老妻来娶他的女儿,爷爷就把来人骂了一通。那个干部气哼哼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一个平时不常来往的本村亲戚,他也种我们家的地,突然来敲门。父亲去开的门,来人说种了你们家的地,平时没有送些东西来,今天送上半袋糠,算是表表心意,放下糠转身就走。如果送来一袋大米,父亲一定会请爷爷出来谢谢人家,但是面对半袋喂鸡喂猪的糠,这不是暗著骂人吗,加上来人走得也匆忙,所以父亲也没有留客。
父亲刚转身,(农村一般大门都开著),那个土改干部带著一队兵就出现了。士兵把宅子团团包围,干部带著三个兵冲进来,指著刚放在门边的半袋糠说,“你们收租,是地主。抓起来。”于是爷爷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几个士兵架起来拖到村中的晒谷场。那个干部当众宣布爷爷是地主,在土改中还敢顶风收租,剥削压榨贫农,立即枪毙。不等旁人说一句话,一声枪响,爷爷就死了。
父亲看出来这是那个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的栽赃嫁祸阴谋,他气不过,对那干部说,我去部队找大哥回来报仇。那干部没想到一个农村人的儿子居然在共产党军队是个比他级别还高的干部,顿时气焰就下去了,要娶新媳妇的念头也吓跑了。趁他慌作一团时,父亲回家包了几件衣服就立刻逃离家去找大伯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在路上时,那个干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一个毒计已经出笼。当我父亲终于找到大伯时,大伯已经被军队隔离调查,因为那个干部已经倒打一耙,通知部队说大伯和叔叔都是隐瞒地主身份,混入革命队伍的剥削阶级,而且谎称老“恶霸地主”是被贫农斗争死,要防止其子女做出反党反革命的行动。
调查的结果是党的秘密,大伯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档案评语。但是他被释放了。不过这“剥削阶级嫌疑”就正式进入了我们家族每一个人的档案。曾祖母先是承受不住冤情憋在心里而疯了,她很快就去世了;姑妈留在农村带著一个不好的家庭成份,最终只能嫁一个最穷最贫农最“红”的人才得以生存;大伯提前复员到了地方,一直得不到信任和提拔;叔叔复员后,年纪轻轻就生病死了。父亲到上海一个远亲开的工厂做学徒,没几年,那个工厂也被“社会主义公有”了。父亲,甚至我母亲和我们兄弟以及我大伯叔叔家庭,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都成了异类,时时受到“特别关照”。
父亲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怕我们兄弟年轻气盛,一不留神说出“攻击共产党领导”的话,招来杀身之祸。父母只是一直鼓励我们出国,不要再留恋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知道自己将走,父亲才如此匆忙把儿子招回去讲出这番秘密,而且关照兄长决不要在中国谈论此事。他也没有说这个干部的名字,可能是父亲不知道这个干部的名字,或者他还在某个官位上,或者父亲已经虚弱得无法再说话。
父亲努力说出这些话,又发起低烧进入半昏迷状态,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父亲至死还带著对共产党残暴统治的深深恐惧!
读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我心中开始透亮,我从压抑中,从对共产党的恐惧中看到了它的必然下场,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不再恐惧了,这个秘密现在成了我的一份财富,我要把它写出来,让更多人认清共产党是这样一些流氓无耻之徒组成的流氓政府,它从一开始就栽赃陷害残害人民,用杀人和恐怖来精神控制、奴役十三亿国人。
中共,我不再怕你,你的末日不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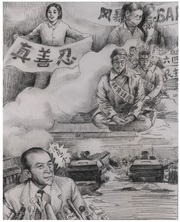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